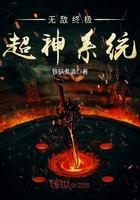我从村子北边的山坡走下河边。(来时是从南边进的村。)半边山在远处,隔着宽阔的水面。对岸是一座山坳,那山坳向里凹陷,弧度恰好同这边的凸起相合,当中神水河弯成一道绿色的月牙,将两岸珠联璧合的接上。
老远就看见舒薇在码头上。
她换了衣服,脱掉了旅行时穿的休闲服,换上一身适于居家和户外散步的,稍稍正式的衣裙。白上衣没有袖子,裙子是同河水一样的深绿色。我疑心那是今年流行的款式,我没有把握,我对女人的衣服基本不懂。她面朝河水坐在栈桥系缆绳的圆石墩上,脚悬在水面来回晃荡。裙裾翩翩,随之波动,水中也有一团绿的,白的影子在动起来。
眼前的景象让我想起夏天江南横塘里,碧波绿叶上盛开的白莲,那是我记忆中水乡最美好的景色。没想到却能在我的故乡重见。
“你一个人啊,陈新呢?”我向她走过去。
她眼睛盯着河水,头也不抬一下。
“脚步轻一点,别吓跑了那些鱼。它们都在睡觉呢。”
果然,岸边有许多小鱼,悬浮在碧莹莹的水中,一动也不动。
“它们多安静啊。”
她深深的叹了口气。
我轻轻走过去,坐在另一个圆石礅上,乘她一心只顾看鱼的当儿仔细看她。陈新不在,我尽可以老实不客气。她长得的确很美,她仿佛是山水化成。不是此地的山水,本乡的山水美则美矣,多少渗透危险的野性:山是奇绝诡险,岩石峰峭如刀,不留神就会摔伤,刮伤,水中更暗藏致命的旋涡,她怎会有这等气质?她是江南的山水,雅秀,温柔,恬静,而且安全。
她的性格在开朗之外,有一点点忧郁。一点点。
半晌没人说话,没有风,水面一朵涟漪也不起。
“温泉水好吗?”我问她,她的长头发还在湿漉漉的。
“好……就是太热,陈新一洗完就嚷累,头晕,回屋说要躺一躺,头一挨枕头就着了。我也觉得飘飘乎乎的,心里有点闷,走出来到水边透透气。”
“你很喜欢水。”
“恩……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山,水太多变,山才让人觉得心里安定。”她抬起下巴,望着对面的山坳。
“那好啊,你正好要嫁给一个山里人,可以如愿以偿了。”
她扭过头来,眼睛闪闪的望着我:“你也这么说?以前有个算命很准的人给我算过命,说我将来一定会嫁给一个山里人。”
“他算得果然很准啊,陈新不就是山里人吗,我们省的人都是山里人。可惜陈新要做倒插门女婿,山里人投入水乡的怀抱,变成水里人了。”
我打趣她,她笑得咯咯出声,又问我觉得陈新这个人怎么样。
“好啊,很不错,他人很实在,大方,又活泼……呃,我的意思是,开朗风趣……人长得也挺精神,别看他粗枝大叶,其实蛮细心的,对你那么体贴……呃,女孩子嫁这样的男人,是有福气的。”
每到恭维别人,我的口才就下降,尤其是一位漂亮女孩的幸运男友。这一番结结巴巴的套话没能让舒薇满意。
“是吗,别人倒也总这么说……可也有人说他性格伧俗,气质差,老是嘻嘻哈哈大惊小怪,不稳重。你看呢?”
我怀疑那所谓的“有人”就是她自己,这个年龄的女孩总爱求全的。我在肚里搜着词儿,在说真话和不得罪人之间寻找平衡点:
“呃,怎么讲,体育运动出色的人,总容易给人留下这种偏见,他毕竟是足球队的后卫嘛,又不是诗人。只有你们这种还在念书的女孩子,才说得出什么气质不气质的话,等到将来毕业工作,结婚抱娃,你就不会嫌他气质不好,只会嫌他赚钱太少了!”
我们说笑着,沿着河岸散了会儿步。话题从陈新,到舒薇自己,到大学生活种种,此时气氛同车上不同了,彼此相熟的程度愈深,谈话的深度愈深,态度愈随便。我们一起谈江南,谈那座长江之滨的名城,六朝金粉的古都。然后又谈到我。
“你还真不象个山里人,比陈新还不象。”她说。
“对一个山里人说他不象山里人,在外人听来是一种恭维,在他本人可不这么看。”
“你比陈新还爱多心。我可没半点瞧不起宝乡的意思,这你该知道。”
“陈新是爱多心的人吗?我没看出来。”
“怎么不,别看他嘻嘻哈哈,心眼可多着呢……你们省人的脾气就是多疑,好多心。”
“是啊,那是一种原始本能,来自遥远的狩猎时代。深山老林里危险重重,到处是敌人,不得不加点小心。只有你们江南人,才以为山是安全的。”
“你不也是半个江南人吗?你在江南呆了那么久,不但气质,连长相都像我们那边的人了。”
我大笑:“我可是正宗本地苗子!哪里有一点像你们江南人。我倒觉得我和这里的人长得挺相像,”我指了指高坡上面,“这里,镇山村。”
“像吗,看不出来。”她仔细的打量过我,摇头说。
“要是我告诉你,我就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呢?少小离家老大回?”
“不,你不可能。”她果断的说。
“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他们的那种,‘气质’?”
我笑着问她。
“不是气质。很简单,假如你真的是从这村里出去的布依族,你一定一进村就投奔你的亲眷,而不会跟我们一道去村长家挂单。”
万没料到她会说出这话来,仿佛一记重锤,稳,准,狠的砸中了那颗暗处的钉子。情绪一下子泄空了,胸口堵得说不出多难受。
半晌无语。我掏出烟盒。很久没想起来要抽烟了,从骑马,进镇山村,到现在。
“可以吗?”
“请随意。”
我掏出打火机,这只烟蓝色的打火机可是我的爱物,随我走南闯北。
“Zippo哎!”她惊叹道,“这一款可不便宜,陈新想了很久,都没舍得买。”
“陈新不抽烟,要打火机做啥?我就这么一点点嗜好,反正光棍一条,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偶尔奢侈一回。”
我啪的打了下火,没点着。
“你一个人?也许我不该问——你,没有结婚吗?”她小心的问我。
“没有。”
“女朋友呢?”
“没有,”我又打了下火,还是没点着,“目前没有。”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
“那,你的父母——”
“都去世了。”我平淡的答道。我被这打火机弄得有些不耐烦:“邪了门了,怎么回事这是?”
“不会是假的吧。”她伸头看那只出故障的打火机。
“开玩笑,正版Zippo,托人从香港买的。难道没油了,才加过的呀?”
“我们的相机也老不闪光。我知道为什么。我懂一点风水五行的知识,你看这里到处是水,说明镇山村是属水的,所以克火。”她颇为认真的分析道。
“镇山村克火!这个解释很妙啊,”我被舒薇的风水五行知识逗乐了,“那他们只好寒食了,怎么生火,煮饭?我估计是湿度太大,对精密仪器有影响。”
“打火机也算精密仪器吗?”
“一般的不算,但我这是Zippo,娇贵,所以算。”
我笑着说。人在抽不成烟的时候最犯烟瘾,我烦躁的踱了几步,一眼望见对岸的山坳,忽然间引出一个念头来——对呀,应该去河对岸瞧一瞧的。
“舒薇,”
“哎,”
“你想不想到对岸,探一探险去?”
“探险?”她眼睛一亮,“村长不准我们去河对岸啊,还有,你知不知道,对岸在闹鬼呢!”
“对岸在闹鬼?你听谁说的?”我狐疑的看着她。
“听村里人说的。说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神水河对岸的山里面就要闹鬼,叫千万别过河去。”
“哦,我怎么不知道?那更值得一看了——除非你不敢,那就算了。”
这明显的激将令舒薇做了个“不屑”的表情,她拢拢还在滴水的头发,望肩上一甩:
“谁不敢?其实我早就在心里盘算了,正想着怎么跟你说呢——可是船呢,你这水边的民族连条船都没有,难道要我们游泳过去吗?”
“谁说没有船?是你眼力不够,那边不就有一条船吗!”
十步以外的岸边,长着两棵大柳树,枝叶拖到了水面,绿荫间很隐蔽的露出一只船头。
船上有人。那是一个渔夫,天没下雨,他却怕冷似的浑身埋在斗笠和蓑衣当中,坐在船尾钓鱼。他听明白我们的意思,和许给他的五块钱船钱,若有若无的答应了一声,起来放我们上船。船是独木船,长而窄,船头尖尖,宛如一片竹叶,中间搁着三块横木,各自够坐下一个人。
舒薇想起陈新,打算回去叫上他。
“你叫上他,撂下谁呢?看见没有,这船只够三个人坐。”
“倒是……那咱们回去以后,谁也别说啊,要不然他见咱们有得玩不带他,肯定会生气。”
“有数有数。其实,陈新不在也好,否则,”我故意的说,“以他那种‘伧俗’的性格,老是嘻嘻哈哈,大惊小怪,多半会败坏探险的气氛,岂不可惜。”
舒薇知道我在笑她刚才的话,也不在意。我扶她坐好,渔夫船桨一点,小船离了岸,无声的向对岸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