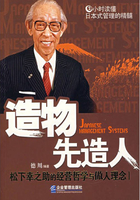人口向城镇集聚还能创造出规模庞大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有利于推动社会化分工以及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的产出效率。此外,城镇化也能为产业发展创造平台。当前,很多产业必须放在城镇化的大平台上才能有大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许多新兴产业如新技术研发、IT业、现代金融服务业等,需要依托城市才能获得扩张能力。城镇化带来的产业繁荣与高投资回报还将吸引更多劳动力、资本、技术的流入,这些要素的相互碰撞与整合,将进一步推动新技术的创新与转让,促使新兴产业发展与城镇化互动。
跨国经验研究也表明,在经济发展承载范围内,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耦合关系。平均而言,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的简单相关系数可高达0.85。例如,19世纪初,美国仅有约5%人口生活在城市。随着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关产业和制造商在城镇集聚,1960年70%的美国人居住在城镇,而城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城镇化发展过程既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也是一种主动性战略安排,这两方面都不乏成功的案例。前者如欧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大体是伴随着工业化孕育、发展、成熟的自发演进过程。工业革命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为从轻纺工业、重化工业到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大量新兴就业机会,而且一些煤铁资源丰富或水陆交通方便的地区,由于工业生产与产业工人的集聚又加速了城镇化进程。后者如日韩等国,为加快“二战”后的经济复苏,日韩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韩国20世纪50~60年代,就主动实行政府主导的不平衡增长战略,推进以低工资为基础、轻工业为中心的出口导向型开放政策,吸引了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入城市。为优化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大量法律法规,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并实施了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分别从产业发展、社会福利、居住环境、村镇建设、城乡一体化等方面提出战略目标,促进城镇化发展。
当然,国际上忽视经济发展可承载能力、过度超前的城镇化也不乏其例。例如,20世纪50年代末,拉美地区忽视经济发展水平,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2000年拉美城市化水平达到了75.3%,仅次于北美,超过了欧洲与大洋洲,是亚洲的两倍。就世界范围而言,城市化率占工业化率的平均比值不到1.5,而拉美则超过了2.5,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缺乏工业化支撑,大量进城农民找不到工作,城市贫民聚集加剧贫富分化,“城市病”至今积重难返,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
总体看,城镇化发展与经济转型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经济增长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环境和基础条件;反过来,城镇化的推进,也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促进国内需求和第三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同时,在经济发展可承载范围内,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是一个相互协调的过程,无法人为加速推动。但这并不排除在经济发展可承载的前提下,政府可通过制定一系列战略规划加速推进城镇化,从而更主动地与客观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这在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当然,如果主动的城镇化走向另一个极端,政府脱离经济基本面,刻意“经营城市”,不顾成本地过度扩大城市和开发区规模,也会造成土地城市化泡沫,引发政府信用对未来现金流的严重透支,“城市病”蔓延,反而“欲速则不达”。
城镇化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与工业化程度相对应的城镇化水平低、潜力大。积极稳妥地推动城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
扩大内需
城镇化是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强大动力。大国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内需主导型经济。过去30多年来,我国消费保持了迅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8%,但相对于投资和净出口,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仍有所下降。如果这一状况可以改观,能对健康的城镇化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通常意味着消费水平的提升。经验数据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低于城市居民。据统计和相关抽样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乡村、中型城市、大型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比值大约为1∶2∶3。即使消费水平原地踏步,城镇化拉动消费的潜力也十分可观。有专家测算指出,每1%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我国居民消费总额提高0.19%~0.34%。[2]事实上,近年来家电、家具、建材、机动车、贵金属消费的迅速增长,既有政策刺激因素,客观上也是城镇化发展带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必然结果。
第二,城镇化过程中伴随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带来劳动力收入的更快增长。收入是消费增长的基本动力。城镇化过程中伴随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转移,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收入水平得到相应提升,进而拉动消费。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的第一阶段,以及1万~1.5万美元的第二阶段时候会止跌反升。我国消费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曾经历了两次明显上升,这两个阶段分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明显提升的时期。总体看,我国正经历城镇化从第一阶段(工业化占比迅速上升)向第二阶段(第三产业占比明显上升)的过渡时期,2013年第三产业占比已超过第二产业,这一阶段也正是人均收入水平从6000美元向10000美元过渡的阶段,产业结构转换带来的收入增长和消费扩张效应正处于加速释放阶段。
第三,城镇化带来的消费扩大,能够有效提升工业产能利用率。我国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大量工业产能需要通过外需消化。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多种因素影响,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在这一格局下,通过有效提升城镇化水平无疑对提升最终消费水平,化解产能过剩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仅对于扩大消费,城镇化发展也是拉动投资的重要力量。过去10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已达到GDP的10%,城市建设投资在2008年至2012年间达到高峰,占到GDP的3.5%。过去30年间,每增加一个城镇居民所需的城市建设支出显著增加,从1980年的294元增至2007年的6.4万元,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004年的9%增至2013年的17%。随着新型城镇化更强调以人为本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建设对投资的拉动作用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据财政部财科所测算,城镇化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公共投资需求占比将上升5.9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因工业化和城镇化所带来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约为30万亿元左右。另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测算,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人均公共支出至少10万元。按2015年市民化率达到54%的目标,即实现约2亿农民工市民化,所需公共支出累计将达20万亿元左右。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日益推进,这些潜在投资需求将被不断释放出来。
缩小城乡差距
长期来看,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公平发展。城镇工商业的发展,既为农产品创造了市场,也为农村土地开发与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资本。在农业生产人口下降且日益老龄化的形势下,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居民,将为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空间;让城市工商业资本以商业理念,采用新技术与机械化,整合农业土地经营,将显著提高农村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农村人口的人均收入。这一过程也说明,解决“三农”问题,主要还需依靠城镇化途径减少农业人口数量。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及农业科技的发展,大大激发了生产力,不但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使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有机会到大城市及沿海发达地区工作,而城镇化进程恰好为吸收这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创造了空间。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镇,必然伴随着农业经济活动比重的下降,同时非农经济活动日益活跃。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水土资源紧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推行,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这是“三农”问题的根源。我国人均耕地仅0.1公顷,农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约0.6公顷,远远达不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门槛,城镇化对集约利用土地、发展现代农业腾出用地空间的潜力很大。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增加,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生活水平。城镇经济实力提升,会进一步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形成了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一批城市群,有力推动了东部地区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增长极。但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中西部城市发展明显不足。目前,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2.2%,而中、西部地区只有48.5%、44.8%。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加快,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展开,促使人口经济布局更加合理、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从供给方面看,城镇化发展不仅能带动制造业升级,而且也可以推动服务业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服务业与其吸纳就业比重都将有一个明显上升过程。1970~2009年,OECD国家制造业比重由25%降至15%,其中制造业大国德国也降至21%;同期仅传统服务业就业比重就上升到49%,其中德国、韩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几乎翻番,德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72%。除传统服务业外,直接服务于制造业的生产型服务业也迅速发展,金融等服务业占GDP比重由15%上升到26%,其吸纳就业比重也由6%上升至15%,制造业增加值来自服务业的比重超过30%,其吸纳就业的40%来自科研、会计、法律、管理和文秘等服务业。反观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同时人均GDP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发展潜力巨大。除对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外,城镇化还有利于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供给水平。尽管我国目前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10%左右,但农业劳动力占比仍高达36%,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第三产业的28%。未来随着数亿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供给能力同样具有巨大提升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