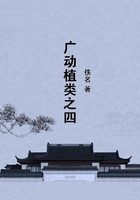与此同时,中山市小榄镇的一个28岁的年轻人——何伯权也开始受镇政府之命来投资办厂。何伯权做过农民、工人、售货员、教师、机关干部,当时刚任镇制药厂副厂长。希望年轻人有所作为的镇政府拿出95万元交给何伯权,让他开办新企业,以便给小镇经济创造新奇迹。何伯权站到了人生的一个新舞台上,除了95万元及几个合作伙伴,他别无所有,一番权衡,他看上了当时热火朝天的保健品市场。
广州乐百氏虽然有了一个好名字,但创业者们深知,好名字并不能托起一个好企业。即使太阳神,其成功的因素也并不仅仅在于企业形象。此时的乐百氏想要与太阳神抗衡,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他们需要同盟军。
机缘让何伯权和乐百氏连在了一起。广州乐百氏与小榄镇工业总公司在此背景下合资成立中山乐百氏保健品有限公司,何伯权任总经理。广州乐百氏以乐百氏品牌许可权及20万元资金入股,占1/3股份。合作一年后,为了全面主导企业的发展,小榄镇方面决定买下广州乐百氏持有的1/3股份。经协商,这部分股份折价为380万元,何伯权从此完全掌握了中山乐百氏的经营管理权,但乐百氏商标的所有权仍在广州乐百氏公司手里。何伯权对乐百氏在奶类制品领域的商标使用权,期限为10年,从1990年到1999年,整整一个90年代,何伯权就像是乐百氏的“养父”,将乐百氏从其“生父”处领养过来,精心培养,期待它能长大成材。
乐百氏成长得太快了,每年近乎翻一番的增长速度快得让人惊喜,也让人不安,因为对这个品牌做出最大贡献的中山乐百氏却没有这个品牌的所有权。
何伯权一开始就对乐百氏商标喜爱备至,以致从未想过真正来创自己的品牌,随着中山乐百氏公司的发展壮大,“乐百氏”已成了何伯权事业甚至情感的一大部分,这三个字浸透了他的心血和汗水。当时他没有钱打广告,于是每到一个城市,他就和他的伙伴们买来大红纸写成横幅:“热烈祝贺乐百氏奶投放市场!”一个晚上穿街走巷贴满整个城市。对这个书写了无数次的名字,何伯权又如何能轻言放弃!
广州乐百氏不但可以自己生产“乐百氏奶”,还可以将这个品牌租给别人生产“乐百氏奶”。时光转到1992年,中山乐百氏的全年产值已达8000万元,何伯权不得不为他掌管的这个企业思考一条后路:数年后,如果不能使用乐百氏品牌将怎么办?中山乐百氏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品牌。
“今日是历史和未来的分界点,今日的结束是新的今日的开始。”对自己从北京大学亲自征集来的“今日”商标,何伯权十分满意,而“今日”的特殊内涵也反映了何伯权对乐百氏的一种复杂心情。他对乐百氏仍珍爱备至,但又不得不让它从自己的事业中渐渐淡出,而全力以赴去推广“今日”。
1992年,中山乐百氏保健品有限公司改名为广东今日集团,但乐百氏奶仍是集团的主导产品。为了尽快推广“今日”,何伯权招来了广告学博士,团结了一批广告人,其宣传攻势在1994年达到了顶峰。“神话人物”马俊仁将“马氏营养配方”的“生命核能”卖给了何伯权,而何伯权通过媒体的炒作,“今日”的知名度迅速上升,“生命核能”俨然可与“乐百氏”分庭抗礼。
贤人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1995年“生命核能”正要大举出击,却遇上了全国保健品市场的大崩溃。这一年,马俊仁也与其弟子不欢而散,“生命核能”没能引起连锁反应,更无法单独托起“今日”。相反,这一时期的乐百氏奶依旧红红火火,蝉联全国乳酸制品销量第一的桂冠。此时的何伯权,内心充满了矛盾:这边“生命核能”有心栽花花不成,那边“乐百氏”无心插柳柳成荫。看来,何伯权此生注定要与乐百氏有缘。这种情感的联系在他心中所占的分量,或许并不亚于利益对他的影响。“生命核能”代替不了“乐百氏”,“今日”也代替不了“乐百氏”。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斩断何伯权对乐百氏的“亲情”,他必须拥有它。
1996年,何伯权向广州乐百氏开出了1500万元的高价,要完全取得“乐百氏”商标在奶类制品方面的所有权。当时经营处境在走下坡路的广州乐百氏很快接受了这个价格。从此,它再也不能向别人授权或自己来生产乐百氏奶,乐百氏奶被正式“过继”给了何伯权。
退出了奶类市场的广州乐百氏当时还有另一主导产品:乐百氏矿泉水。尽管水和奶各有其主,但借助“乐百氏”品牌的威力,水也畅销不已。一时,双方似乎相安无事,但是半年后,一个意外的插曲出现了。
1996年夏天,乐百氏矿泉水在其主要市场湖北遭重创。不少假冒乐百氏之名其实是从水管进来的“矿泉水”,使得正在抗洪抢险的解放军战士大闹肚子,而实力弱小的广州乐百氏无力应付这种局面。媒介曝光后,“乐百氏”的名声一落千丈,水的形象连累了奶,广州乐百氏的黑锅要中山乐百氏背,不少舆论把矛头对准了中山乐百氏。毕竟,没有多少人知道:此“乐百氏”非彼“乐百氏”。
何伯权决心向乐百氏不争气的“生父”最后开战,他要全面收购广州乐百氏。但广州乐百氏不甘就范,还有抵抗的余地。
在香港,中国儿童营养保健品市场的两个最主要的对手——中山乐百氏的何伯权和杭州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举行了一次悄悄的会晤。当时“娃哈哈”是在两条战线上与“乐百氏”交战:在奶类方面是与中山乐百氏,在水的方面是与广州乐百氏。何伯权希望借宗庆后之手在瓶装水领域猛击广州乐百氏,使其无法抵抗下去,这样他也可以顺利收购。而宗庆后则看到了一个光明前景:娃哈哈去此强敌,将成为中国瓶装水的龙头老大,各有所得,皆大欢喜。
不久,在武汉出现了大量低价的正宗娃哈哈纯净水,名声已严重受损的乐百氏矿泉水全面溃退,广州乐百氏面临生存危机,再没有与何伯权讨价还价的余地。于是,1997年3月,广东今日集团(即中山乐百氏公司)与已在市场上一落千丈的广州乐百氏公司签署文件,今日集团完全收购了广州乐百氏。
让宗庆后始料不及的是,完成了“品牌统一”大业的何伯权迅速进军瓶装水市场,投资2亿元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生产“真正”的乐百氏纯净水,并重返武汉市场一举成功。
宗庆后与何伯权在年龄上相差将近20岁,而在性格上则均属于内秀型,平日寡言善谋,擅长吸收,敏于变化,并且在重大时刻能果敢决断,不惮于冒险。而在竞争手段上,两人都喜欢鸣鼓而战,不好使小阴谋,对一些不入流的阴招、损招更是不屑一顾。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职业性格使他们具备了成为顶尖级企业家和营销大师的素质。
有一则故事颇值得在这里记录:有一年,一个亡命之徒为了向企业要挟钱财竟在娃哈哈奶中投毒,导致两名小学生生命垂危,而国内一家报纸在未对事实进行彻底核实的情况下擅自刊出了中毒新闻,一时间有五六家媒体进行了转载。
恶性事件发生时,宗庆后正在国外考察,当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打给宣传部门,希望制止这一极易形成模仿效应的新闻继续传播;另一个便打给了何伯权。何伯权当即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的营销公司,严令不得传播、转载这一新闻。而彼时,一些小的果奶企业却以为天赐良机,纷纷把刊发中毒新闻的报纸广为散发,或传真给有关的经销商。
日后,有记者问何伯权,你为什么不抓住这一“机会”打击一下娃哈哈?何伯权说,这种恶性事件的扩散是对整个果奶市场的伤害,乐百氏如果借此机会贸然出手,其结果是往自己的脸上打重拳。
透过对这一突发事件的理性处理,宗庆后和何伯权的战略意识和健康的对手观可谓一览无余。宗庆后常说:
企业家个人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企业的品格。一个正直、有责任心的企业家造就的是一个有长久发展能力的企业。
吴晓波、胡宏伟在谈到娃哈哈与可口可乐的可乐大战时,曾说到一个非常令人动容的宗庆后“做人”细节:
2000年2月27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秘密报告攻击最流行甜味素》的爆炸性新闻,“揭露”美国全国饮料协会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已发现在可乐等汽水饮料中常用的甜味剂“阿斯巴甜(Aspartame)”能分解出甲醇、苯丙氨酸等有毒物质,影响人体大脑的正常工作。报道引述最新解密的一份“秘密报告”指出,阿斯巴甜有改变消费者行为的作用,诱使消费者饮用更多含有该物质的饮料。这篇报道还说,包括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在内的许多世界著名饮料厂商至今仍在使用阿斯巴甜。
2月27日,国内一家报纸首先转载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消息,并通过其电子版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随后几天,“可乐含有对大脑不利成分”、“两大可乐甜中带毒”等触目惊心的报道迅速蔓延开来。一夜之间,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被卷进危机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