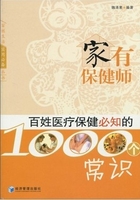然而人是更加凶残和狡狯的,人对你的危险远远大于你的偷吃几只鸡的冒险,他“人”就是你的地狱。正当你高高在上地愉悦着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一家养鸡的人制定了对付你这不速之客的可以称为“边疆之狐”或者“边疆风暴”方略。人最容易萌动的就是杀机。你不知道,你毕竟入世太浅,见事太有限。你照旧在那一天深夜出行,你来到了一家鸡窝前,你突然发现就在鸡窝前弃置着一块羊肉——你就不想想,一块好肉怎么会放置在那里!你快乐地吃起了那块肉……
肉刚刚被你嚼了两口,你已经感到了事情有点不对劲。先是上腭后是下腭被狠狠地刺痛了,然而,你仍然没有警惕,你已经习惯于吞食带着骨头的活食,你张大了自己的喉咙,想干脆把肉吞下去。就在这时,接连几下的刺痛使你呆木了,你忽然明白,你中了计了,你的喉咙已经被鲜血堵塞,你的血管已经一个又一个地被刺裂被撕开了。你的动脉流出了汩汩的鲜血,自己的鲜血使自己窒息,鲜血流到了鼻孔里,鲜血流到了耳朵和眼球上,你的眼睛睁得老大,你知道,你完了。
孩子,你临终的时候想起了你的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羊肉里有七根针。这七根针刺破了你口腔和喉咙的粘膜、皮肉、静脉和动脉,刺破了你的气管和食管,卡住了你呼吸的通路,最后结果了你的性命。
你的死亡不光彩。你的身体因为恐怖和疼痛缩成了一团,再极度伸长,僵硬,固定在那里。你的尸体像是一条四条腿别在两端的破板凳。你的面孔因为痉挛和挣扎全变了形。你不像一只猫而更像一只缩小了的狐狸。你的皮毛立即污秽不堪,并且结成了一球球的疙瘩。
……那天清晨你没有按时回家,钱文十分惦记你。六个小猫吱吱地叫。
说也巧,那天是你的孩子们一周月生日。它们已经可以开始吃点什么,于是钱文给它们用剩肉汤拌了米饭,它们不太爱吃但也多少吃了一点。天已大亮,你仍然没有回来。你本来每天都是天一麻麻亮就回家的。钱文觉得不妙。他自己磨叨。东菊说:“过会儿它就会回来的。”她老是把世上的事情看得那么简单。
然后是中午,然后小猫崽吱吱叫个不住,然后东菊也开始磨叨:怎么还不回来?然后是下午四点半,钱文听到一个邻居说是水渠支渠边发现了一只死猫。他觉得不祥,他不能决定要不要过去看一下。也许是他不敢去看,他怕当真是你。最后他来了,他已无法辨认,谁也无法辨认,比起活着的时候,死猫显得瘦长、丑陋、僵硬,一点可爱的劲儿也没有了。一切死了的生命都令人觉得它该死。他的心怦怦然。
然后是晚上,钱文说:“我怕是出了事儿。”东菊说:“不会的,一会儿就回来了。”然后钱文回忆,他模模糊糊地记起似乎已经有一次你晚归四五个小时,是不是有过这么一次?那天中午了你才回来,身上有伤。他只想到你可能是被顽皮的孩子捉住,你可能受了苦。他根本没有想到你会受到人的精心策划的算计。他甚至想到,是不是有过关于猫偷鸡吃的警告。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也许那真的不是你?一连十几天他们还做着你突然归来的好梦,他们总觉得不至于,他们总觉得你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也许你再次遇险,被顽童捉住甚至被拴了起来,但是以你的聪明,最终还是能够摆脱羁绊。他时时听到你的叫声,他一天好几次突然跑到门外疯狂地大叫“皮什皮什”,他甚至梦里也与你再次相会,在梦里他抚摸着你的皮毛,他叫着你。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许多天过去了。钱文也好东菊也好,都明确了,那只变形的难看的死猫就是你。
……于是他们把对你的纪念变成精心照顾你的孩子的实际行动。钱文用眼药瓶往它们的嘴里喂牛奶,钱文给它们点眼药水。钱文每天清扫它们的屎尿,眼看着它们成长。钱文自称是猫的代理妈妈。
然而你的孩子们的命运也都很不济。可能是你太聪明了,一只猫太聪明和一个人太聪明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不祥。你占用你的家族的灵气运气占用得太多,于是你的孩子们大多都有点智力方面的困难,而且都是苦命。你的大儿子,一只小公猫又傻又脏,钱文给了一个朋友,但是那个朋友不久就把它抛弃到距离此地一百多公里的外县去了。你说它傻吧,一个月后,这只脏猫找了回来,找到了老主人钱文的家。这简直难以置信。钱文热烈地欢迎了它。
钱文与农民们讨论一只猫何以能够认路,农民们说是猫会观察星星来辨别方向。从此钱文心里常常出现一只孤独的小傻猫在房顶上夜观天象的镜头。他感到神奇——这也近于恐怖。
没几天,这只似乎善于夜观天象的猫就使他们难以容忍了。由于它随地便溺,臭气熏天。它尤其爱吃人的分泌物,由于边疆气候变化剧烈,人们常常会因呼吸道不适而吐痰或者擤鼻涕,而这只傻猫一听到有吐痰声或擤鼻涕声,就娇啼婉转着跑过来等吃。这种嗜痂成癖的习性令钱文发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何况猫乎?后辈的面子毕竟有限。钱文再次把它装到一个书包里,骑上自行车走出去了好几公里,把它抛到了一个门口有军人站岗的重要机关的后花园里。回家路上他有点后怕,他怎么把猫“派遣”到机要单位去啦?如果拍下一张照片,也许会判定他是在做什么非法勾当。接下来它怎么样了呢?被收养?被处决?沦为野猫、冻饿而亡?
你的另一个儿子更加吓人,它的爱好是往灶火堆里钻,从十月份它就钻起灶火来了。它为什么那般怕冷?为此钱文用纸板把灶火坑盖死,当然,这有引起火灾的危险。最后,不是纸板而是你的这个扑火的儿子燃烧起来了。它差不多可以说是自焚身亡。
另一个儿子是一个聋子,它长得不错,略具乃母之风。但是它听不到唤它的声音。它被钱文给了出去,据新主人说,它没呆住,丢了。总之,来之于空冥,去之于茫茫,不明下落。
你的一个女儿看来身强力壮,它才一个半月大便早早爬上了门前的杏树——你当年就是从那里大胆地向前走的。它上了树却不会下来,钱文愈是接应它它愈是往远里跑,它最后冒险往下跳,摔折了腿,后来死了。
你的另一个女儿是个小贼,什么都偷,什么都舔,什么都弄脏。给它喂食的搪瓷盆子里,经常剩着小鱼和肉馅拌的食物,而它却经不住偷窃的诱惑,它最擅长的是钻到邻居家偷烤饼。当地习惯,一次烤出大量半发面饼,放置在悬挂在房梁下的木板上。所以悬空放饼是为了便于通风,也为了躲避老鼠的骚扰。但是此猫不知以怎样的技巧爬到了半空中的木板上。它吃得很少,但要把所有的烤饼糟蹋一个六够,为艺术而艺术。它屡干不爽,其乐无穷,足以把当地居民气死。后来它被钱文的邻居处以了死刑。不是阴谋,而是公开宣判,公开处死。这亦令钱文心怦怦然,钱文觉得实在对不起你。
你的最后一个女儿其实最像你,它本来有希望继承你的风范和智慧,而且,它比幼时的你更加秀丽。它是一只三色猫,白底儿,黄与黑的斑点。它叫唤的声音也极温柔雅致,富有人文色彩。它同样的洁身自好和善解人意。它是你的最后的纪念,是你给钱文留下的最后安慰。钱文戏称之为小公主。一天,它在廊子上晒太阳,突然从墙头上跳下一只大狼猫,狼猫向小公主扑去,把它扑倒在地,不知意欲何为。公主还十分幼小,不大像施暴的对象。但或许强者的威风全在于摧残弱者,面对弱者、未成年者,才有威风,如果是面对更强者,强者的威风何在?猫性正是如此。狼猫被东菊轰走了,小公主奄奄一息,瘫痪在地。
我们一定要救活它,东菊和钱文说。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给小公主喝牛奶羊奶,给它吃肝吃肺,给它吃生鸡蛋。果然几天后,它初步恢复,能够起身走路了,但走起来有点歪歪晃晃。
一天晚上,正在喝饭后的砖茶,钱文和东菊听到了奇怪的惨叫声。儿子说,是小公主钻进了他们夏季闲置在床下的锡铁烟筒里。他们急急地叫唤小猫,愈叫它钻得愈深,惨叫声也愈不忍卒闻。最后,小猫出来了,浑身都是毒性强烈的烟灰和为保护烟筒而抹上的机油。小公主匍匐在那里,只剩了捯气和抽搐的份儿,忽然它厉声惨叫如一小人儿,然后伸腿瞪眼死去。
在北京待了四个月刚刚回到边疆的儿子评论说:“这只小猫儿什么都好,就是有神经病。刚养好了伤,它上哪儿不好,干吗要钻烟筒呢!”
于是好猫全家覆灭,从此断子绝孙。
虎头蛇尾是万物难逃的规律。这只天才的高品位淑女猫氏家族亦是如此。
2000年2月开篇于北京
2003年5月完稿于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2003年8月定稿于北戴河创作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