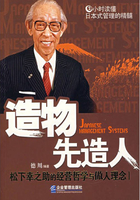中国版图上出现叫“北洋”的军队,应该从1895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起。因为这支新军归北洋大臣节制。1901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因而,所建军队便称北洋军。辛亥之役,清帝退位,共和兴起,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所建的这支北洋军便成了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握有控制权的军事集团。1916年袁世凯病死了,他的那支北洋军队因为受着东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钳制,遂分为以皖人段祺瑞所指挥的皖系,以直人冯国璋、曹锟所指挥的直系和以奉人张作霖所指挥的奉系三足鼎立之势。于是,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大混战的高峰期。1920年7月发生的直皖大战,皖系出动五个师和四个混成旅组成的定国军,段祺瑞任总司令;直军以一个师九个混成旅组成的讨逆军,吴佩孚任前敌总司令,激战四日,皖军大败,段祺瑞宣布下野。北京政权为直奉两家共有。1922年4月下旬,由于分赃不公发生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张作霖指挥四个师、九个旅约十二万奉军,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吴佩孚指挥七个师、五个旅约十万直军,自任直军总司令,两军从长辛店始拉开战幕。至6月上旬,以奉军之败结束。至此,北京政权落入直系之手,为曹锟的总统梦辟开了大门。
得天下的人总想得大位。曹锟不安于“保定”一隅了,他想据有北京。可是,曹锟有一点并不自量,他手下的直系人马并不是团结得如同一人——曹锟在保定做“总统”梦时,吴佩孚回洛阳去营造他的“中州”去了。吴佩孚的信念是:只有用武力统一了天下,天下才能所属,“花钱买议员的选票,那是不牢固的”。但是,吴佩孚看透了曹锟,知道他非过几天总统瘾不可,说是说不服他。“咱们暂时就各走各的吧!”于是,直系队伍在不声不响之中分出了曹锟的“保定派”和吴佩孚的“洛阳派”。
到洛阳去的吴佩孚,凭着富饶的中州,一心去经营他的武装,梦想走自己的“武装统一中国”路。于是,在自己书房的门楣上新张起一副能表白心迹的对联:
龙泉剑斩血汪洋
千里直驱黄河黄
曹锟迫不及待。六十岁的人,无法再慢慢悠悠地等下去。天津回来之后,心情尤急,兄弟们都愿意出钱了,有了钱,赶快买(总统)不就完了?他偷偷地在密室中打开保险柜,取出从北京秘密带回的一包总统印——他舍不得把它们留在北京,他真想把它们一颗一颗都系在腰带上。若不是怕不保险,他准会那样做。就这样,他只要走进密室,总要把保险柜打开,亲昵地把它们一颗一颗地抚摸个够,然后再谨慎地锁起来——,一颗一颗地又抚摸起来。那颗颗闪着金光的大小“疙瘩”,不仅灰尘让他摸光了,印文的朱砂红泥也被摸光了,他虽然还不曾用它们印在什么公文上。他多么急想用它们呀,那可是世界上最光彩的事情。
曹锟又过了一阵“抚摸总统大印”的瘾,还是轻轻地、无可奈何地叹息着,再把它们包起来,放回原处,重新锁上保险柜的门。“什么时候才能不锁呀?”
锁好了总统大印,曹锟觉得“应该马上干点实事了”。他从密室走出,对身边的侍从说:“你把副参谋长王养怡找来,我有急事。”
王坦,五十多岁的人还是一表清秀,连流行的小八字胡也不留,虽担着军中副参谋长之职,却很少军装打扮。早年,长衫小帽,有时还拄一根文明小棍,俨然一副名流绅士;近年来,却又多是装束西化,穿起马裤和胸前有排扣的西服,足下自然有一双锃亮的皮鞋,文明棍不见了,多了一只公文包包。此人年富力强,行动敏捷,思维敏捷,又善于谈吐,是京、津、保颇有点名气的名士派人物。虽然在吴佩孚眼中并不十分高大——吴佩孚的儒家的眼光批评他华而不实,说他是个只注重修饰外表而腹中空的花花公子,认为他只能败事,不能成事——,但在曹锟心里,却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才,不可多得的人才,值得信赖的人才。这样,便应了那句“人以群分”的俗话,王坦成了曹锟的座上客、心腹。
王坦来到曹锟面前,寒暄几句,便竟自坐在一旁,等候他的大帅“交代任务”。
“养怡,”曹锟对他的部将从来都是直来直去,“这阵子我只在京津忙忙,不知你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见吴大头了?”
王坦心里一惊,心想:“你钱不着落,八字没一撇,我咋去办事?我事办成了,你两手空空,分文拿不出,我怎么收场?”心里一急,额上便冒了汗。忙拿出手帕,一边擦抹,一边说:“大帅,听说您去天津了,不知那里的事落实得怎么样了?大爷和四爷他们有什么意见?”
王坦软丁丁的一个发问,曹锟心里陡然凉了一下,面色又猛然间添了一点怒:“什么话?我要你办事还能没有钱?老大、老四还能不听我的?我交代你的事你尽职不就完了?”不过,这只是曹锟在心里想,并没有发作出来。他知道王坦是个有用的人,现在得拉拢他,得利用他,得让他出力办事。又想:“可也是,办这样的事,钱不落实也难插手。空口白话,给人印象坏了,下一步也难走。养怡想得不坏。”于是,缓了缓口气说:“养怡,这一点你只管放心,老大他们没有不支持的,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有,用多少有多少。你放心大胆去办就是了。”
王坦笑了。“大帅,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想什么?”曹锟问。
“我是说,这样的事,大爷、四爷他们觉着可办不可办?”
“没问题。他们都说可办。”
“这就好说了。”其实,王坦还是想的钱事。他明白,花钱的事,没有老大、老四开口,十有八九办不成。尤其是老四,此人管钱多,管得又严,是个入钱越多越好、出钱越少越好的角色。现在,既然管钱的乐意出钱了,这经手办事的事,王坦还是乐意干的,何况是这样名利都不薄的好事。“大帅,您放心,大头那里我会尽心的。只是……”王坦说了两句大话,却又留下一个“关子”。
曹锟尚未来得及兴奋,心里便紧了起来。“怎么样,还有难题?”
“大帅,听说‘合肥’跟张雨亭(张作霖号雨亭)勾结在一起,正在上海同孙中山谈联合的事。大概其中就有有关议员的事。”王坦的消息可靠,他不是有意吓唬曹锟。“这几天,议员们纷纷南下,似乎与他们有关,像是去投靠他们。”
“有这事?”曹锟急了。
“有。”王坦说,“消息十分可靠。”
“这么说来,咱们更得快下手。”曹锟皱着眉说,“你把礼品准备的厚点,让他们都能动心。争取留下来。”
“厚?”王坦神情一愣,“厚多少?”
“每人三千元,如何?”
“论理说,三千元也不算少了。”王坦知道,曹氏兄弟这些年捞了不少钱,得趁机抓他一把,便说:“只是,各派都在拉人,多一份礼总是多一分保险。从这方面想,大帅,您看……”
“可以,可以。”曹锟很大方,“你看着办吧。”又说:“尤其是大头那里,务必厚赠一些。”
“我明白。那也得有个适度。”王坦说,“大帅,我看这样,议员么,每人限在五千大洋,也就够了。吴大头那里么,就给他整数。您看如何?”
“你说十万?”曹锟瞪了一下眼。
王坦心里一惊:“难道曹三傻子嫌多?咳,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拿着铜钱当镜子!”忙说:“大头这个人,别看能耐不怎么样,位子在,议会的成员还是听他左右的。少了就怕动不了他的心。”
“养怡,”曹锟笑了,“我素来敬佩你的胆识,今天怎么有点英雄气短了?办这样的大事,捧着十万八万,先不说别人动心不动心,咱自己的身架也不够气派。这样,你先拿四十万去给大头,不够以后再补。”
“这个……这个……”王坦大吃一惊,“老家伙不惜血本了!”忙又说:“大帅有这个心意,这件事便有十二分把握了。那……我就去办了。”说着,便退了出来。
“你等一下。”曹锟站起身来,说,“这里有两张(银)票,你先拿着支配,时间抓紧点,免得夜长梦多。”说着,拉出抽屉,取出纸包,从中拿出两张汇丰银行的支票交给他。
王坦也不说推让的话,接在手中,笑嘻嘻地走了。
买总统的决心不再动摇了,曹锟真不惜血本了。一旦真的要倾家了,又觉得家资太小、太不够用了——他怕因小有不足而功亏一篑。倒不如宽打窄用,得心应手。因而,他想在内宅也做做工作,请妻妾也出一臂之力。“果然大事成功了,她们都是宫院中的角色了,出点血,也不算多。”这么想着,他便从前厅走出,向内宅走去。
为钱的事,这几天,曹锟可算绞尽脑汁了。昔日,无论从何处弄钱、弄多少钱,他只要有一个眼色、一个示意就行了。比如几宗进项较大的款项吧,都是如此:军饷中的油水,那是由李彦青办的。
李彦青,比曹锟小二十四岁,原本是长春一家澡堂里的小伙计。曹锟是在洗澡时认识他的。那时候,曹锟刚任第三镇统制,奉调长春,常来澡堂洗澡。每次洗澡,总是前呼后拥,咋咋呼呼。李彦青是小伙计,二十岁上下,机灵透顶,一表人才,每次都是围着曹锟团团打转,捶捶背,捏捏脚,推推拿拿揉揉,弄得曹锟通身发酥。不久,这李彦青便被曹锟弄到身边当差。曹锟从长春回保定时把他带回保定,并且把一个家仆的女儿嫁给他为妻。李彦青认乎其真地伏在曹面前,着着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说:“大人,您给小的我成了家,我便把小命全交给您了。日后该我办的事,您只管交代,刀山火海,我都不眨眼。”
曹锟微笑着,说:“该办的事,不是如何交代你,得凭着你机灵的小脑瓜去想。懂吗?”
李彦青点点头。不久,他便升为副官。曹锟做了直鲁豫巡阅使时,李彦青竟当上了巡阅署的军需处处长。这小李动了脑筋:“曹大人让我管军需,军队的衣食住行全归了我,我得动动‘脑瓜’呀!”这小李真不愧是机灵鬼,脑筋一动就有门,每次发军饷,每个师扣两万元作为对大帅的报效,杂牌军还更多一点,谁也不会不答应。那时候,直系的正规军是二十五个师,仅此一项,曹锟的月“外快”收入就是五十万大洋。曹锟笑嘻嘻地收着银子钱,笑嘻嘻地对李彦青说:“小李子,你行。你真行!”
在曹锟的发迹过程中,利用战争发财,已是他惯用的手段了。就说1917年反复辟那场战争吧,段祺瑞委他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任务是由他率第三师从保定向北京进军。进军途中无仗打,等他跑到北京,辫子元帅张勋早已败逃荷兰公使馆。他的军队几乎只是一次不远的行军。到京后,曹锟只向军需处使了个眼色,军需处便向段报销六十万大洋战争消耗。段祺瑞明知是“卡油”,也不得不如数拨给。
最离奇的还有贪。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后,接收皖系物资时,曹锟坚持把皖系骨干分子徐树铮所办的西北边业银行全部“没收”,这可是一个巨大的金融集团,是皖系的经济支柱。有人报告说:“银行中有安福系要人王郅隆、王揖唐、朱深等私人股本一百万元如何处理?”曹锟只瞪了一下眼,这一百万元就姓了曹……
现在不同了,不是从敌对面或国家府库中去取钱,而是要从自己的亲人衣袋中取钱,诈、骗、抢、掠都不行,只能说服,只能让他们甘心情愿,高高兴兴。这件事,非自己出马不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曹锟进入内宅,先向夫人郑氏住处走去。
郑氏,是曹锟卖布时的发妻。如今,已是人老珠黄,足不出室的人了。据说她每日三次烧香念佛,别的啥事也不管。只是,这位郑氏心肠极其善良,家务上也做得大度。所以,姨太太和子女们有什么排解不开的事,总是到她面前,由她论个公道是非。郑氏不问财钱上的事,连自己的吃穿用也不问。曹锟走到她的门外,停足听听,室内静悄悄,门死闭着,门缝里飘过一丝丝松香气味浓浓的轻烟。曹锟索性不想进去了。“她这里,没有多少积蓄。”妻妾们的“私房”,曹锟基本上心中有数的。据他所知,夫人郑氏一生不问钱。天津郊外军粮城的小马厂那两百顷水旱稻田,虽然是以夫人的名义购下的,但一直由夫人的哥哥郑大赣经营着。这位郑大郎舅又是一位吃了清早不问晌午,有仨钱能花五个的角色,这几年不再向曹锟“打抽风”,曹锟已经谢天谢地了,再向他们要点钱?曹锟皱着眉摇摇头——他没有叫夫人的门,只在门外站片刻,便走了。
离开夫人的宅院,他忽然想起了二姨太高氏。“唉,她不死就好了。她会助我一臂的。”
二姨太高氏,天津卫的名门闺秀,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曹锟当营长时以夫人身份嫁曹。嫁后方知曹已有妻室便郁郁不乐,只生下一个女儿便离开了人世。高氏死后,曹锟方知她是带来了巨额陪嫁,唯因郁郁而退还娘家。曹锟为此,也总是深有怀念。所以,人虽不在了,他仍然为她设有专宅,只让遗女士熙和奶娘居住;又因为曹锟特别钟爱士熙,常来照看。今天,为钱事来到宅前,竟产生了忧伤,足未停,即匆匆走去。
三姨太陈寒蕊的住处,是一幢完全西化的小楼,和她模样一样,俊俊秀秀,门外还有一株高大茂密的白杨树,巴掌大的阔叶,随着微风,敲打出“哗哗啦啦”的响声,这响声的欢快,也跟三姨太的性格一样——
陈寒蕊,天津大沽人,是曹锟的同乡,陈氏也是仅次于曹氏的大沽富商。大约是陈氏族长为了寻觅一座靠山或者财产的“保镖”,就在曹锟从东北长春、昌图调回北京、保定时,决定把爱女嫁给他,甘心做姨太太的。那时候,曹锟已经五十岁了,满面皱纹,鬓有银丝。而陈寒蕊刚刚二十岁。这个貌美心高,能诗善画的少女一听说要嫁给一个比自己大三十岁的傻子,顿时痛哭大骂:“我不嫁给他,就是死也不嫁给他。谁不知道曹锟是大沽镇上的三傻子,是个浪荡子弟,五毒俱全;曹家又是地方上无恶不作的人家,讹诈、勒索、抢占财产,没有不干的,我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嫁给这样的人家?”
少女纯真的心被伤害了,她宁死不嫁。
陈家族长却另有心思。祖父、老爹偎在寒蕊身边,揉着泪眼,劝道:“闺女,俺何尝不知把你嫁给曹三傻子是拿鲜花朝牛粪堆上插呢?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大沽镇上,咱是斗不过曹家的。不知哪一天,曹家把魔爪朝咱们陈家一伸,咱们的盆盆罐罐、鸡猫狗鼠全都完了。闺女,别当是嫁男人,就当是为陈家换来个忠心耿耿的保镖,换来个看家狗!咱要他为咱看家守户,为咱保住金银财宝还不行吗?闺女,算是祖上求你了,你当一个咱陈家财产的救命恩人吧。你嫁出的那一天,陈家一定拿出一半家产为你作陪。”长辈们一边说,一边流泪,一个一个泪人儿似的。
寒蕊一见,心凉了——这姑娘也是知书达理的,有些儿心胸。一边流着泪一边思索:“是的,陈家有今天这份家财也实在不容易,几辈人流汗流血、披星戴月、省吃俭用,若是被强权伸手抢去了,也实在可惜。作为陈氏的后人,谁能不珍惜这份家产呢?牺牲了我个人,能保住陈氏祖业,我嫁,我嫁给曹锟——三傻子。”这么想着,便揉揉眼,对身边的家长们说:“你们别哭别求了,我嫁给曹家就是了。”
“闺女答应嫁了?”家人齐问。
“答应了。”陈寒蕊说,“不过,我得提个条件,答应了我的条件,我再嫁;不答应我的条件,至死不嫁人。”
“说吧,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你们告诉曹锟,我要当面跟他交谈一次,谈好了,我嫁给他;谈不好,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谈什么呢?”爹在一旁犯愁了,“一个闺女家,能给人家谈什么呢?”
“爹,你别愁,我想谈的事,我自有主张。”
家人答应了。把话传给曹锟,曹锟笑了:“好一个闺女,未出阁竟敢跟男人面谈条件!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条件,用什么方法谈!”于是,两家相约,便在天津一座大饭庄里举行了这场特殊谈判。
曹锟便装简从,一副相亲相。
陈寒蕊不忸不怩,落落大方。
二人对坐之后,互视片刻,曹锟先开了口。“陈小姐,有什么话,请讲。”
陈寒蕊微笑点着,说:“听说是你托媒向我家求亲的,不知有没有这回事?”
“是有这么回事。”曹锟说。
“不知道你是以第三镇统制的官位向陈家求亲,还是以大沽镇上门当户对的两户普通人家的姻亲来求亲?”
“这个……”曹锟愣了一下,忙说,“既然都是乡里乡亲的,当然是以两个家族来结秦晋之好的。”
“我知道你是有妻室的人,还娶过一位姨太太,死了。曹陈结秦晋,我至多也只是你的一个偏房,姨太太。这我不计较。我得问你一句,你把我娶过去,是作为有情有义的夫妻相待,还是当作下人、婢女?”
“当然是有情有义的夫妻关系,绝不会有任何歧视。”
“是真话?”
“可以对天表白。”
“好,我记住了。”陈寒蕊说,“那么,今后我到曹家了,家庭地位、钱财、交往、喜好,我都得要求自由自在。当然啦,绝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按照规矩,按照民主共和的新生活规矩。”
“完全可以!”曹锟还说,“你到曹家了,我将以夫人的身份请你参加社交活动。”——其实曹锟是没有办法,原配是个托不上席面的女人,高氏又过早地走了,娶过陈氏,自然由她出头露面。
……一切谈得融洽,陈寒蕊成了曹锟的三姨太。
转眼就是十年了,十年中,曹锟果然特别宠爱她,总以夫人待之。陈氏先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这可是曹锟唯一的儿子,那一年曹锟五十七岁。五十七岁得子,再加上直军攻克岳州,双喜临门,曹锟特别高兴,故为儿取名得岳。为曹氏生子,陈寒蕊自然成为举足轻重的女人,在经济上,她也是厚有所积的。就说老五曹钧的北方航业公司吧,陈寒蕊就有十分之一的股金;陈寒蕊还在天津大华火油公司投资十万大洋;曹锐的恒源纱厂,还有曹家在天津、保定的九家当铺,均有陈寒蕊的大股;曹锟还曾以三万元大价在北京炭儿胡同为她购了一所原国公府的住宅。在女人中,陈寒蕊早成了首富。
——曹锟在小楼外驻足片刻,便走上楼去。
刚到“而立”之年的陈寒蕊,一派时装打扮,连头发也剪得齐耳秀气。一见曹锟到了,忙站起身来,理了理天蓝色的旗袍,又从右腋下抽出一方粉红色的手帕,一边轻抹着嘴唇,一边说:“哟!今儿啥风,怎么不请自到了?”
“想念太太你了。”曹锟说,“特来看看你。”
“我不信。”陈寒蕊把脸背过去,只给他一个背影,说,“你这段时间这么多大事,一群能人帮还帮办不完,你会有空来看我?”
“真是特来看你。”曹锟说,“顺便么,也有点小事,想跟太太商量。”
“我说呢。敢情那要‘商量’的小事,才是正经事吧?”陈寒蕊说,“说吧,大事也好、小事也好,说出来我听听。能办的,我一定会帮你办。”
曹锟笑着把准备馈赠议员、拉选票的事如实说了一遍。又说想在她这里挪用点钱的事,然后说:“这钱嘛,只是暂时借出来用用。一旦大事办成了,国库中有的是银子钱,一本几利还你也易如反掌。何况,到那时,你们几人也都是宫中的主了,要什么没有?你想想。”陈寒蕊笑了。“你这事我早知道了,你愿意瞒我,我也装不知。你今儿对我说了,我也实心实意地对你说,事你想咋办就咋办,钱,我分文没有。”
“太太这话就说远了。”曹锟说,“我要是当了总统,你是什么身份?不说你也知道。出钱不出钱,是害还是利?你也知道。不出钱,我也不勉强,那就以后也别怪我封赏时没有你的分子。”说罢,曹锟起身要走。
陈寒蕊急忙转过身来,笑了。“哟,皇位还没坐上,就摆皇上架子了。你走吧,我也不勉强留你。可是,我也得把话说在前,我的儿子绝不领‘太子’衔,看你传位给谁?”
曹锟转过身来,拉着她的手,“乖乖儿”的叫一阵,又说:“我不白用你的钱。我知道你有钱,再说,大沽那边,就是挪个三五百万也难不着。太太,帮我一下吧。”
“到时候再说吧,没多有少,得表表心。”
“我就先谢谢太太了。”说着,同她又亲昵了阵子,这才走下楼来。
下一个去处,自然是四姨太刘凤威的“别墅”。
刘凤威的住室,也是一幢别致的小楼。不过,楼前没有白杨树,而是一片怒放着五颜六色的月季花的花圃——凤威喜欢花,尤其喜欢月季,说它身个儿低矮,无骄姿,或数朵或单花,或深红或淡红或白,总是那么相宜;她尤其喜欢月季花的萼片边缘那派羽状分裂,说那是花的魂!更加上月季花花开的时间长,通身又都是药材。所以,有暇时,她总在花圃间拾叶、采瓣,以备药用。
曹锟来到楼旁时,见凤威又在花圃中走动。知道她在采瓣或拾叶,他想看看她到底有什么新趣。
凤威在楼上坐闷了,想练练曲,也提不起兴致。于是,走下楼来,想和月季唠唠天。月季花又新开了,鲜嫩娇艳,奇容异色,暗麝著人!“啊,怪不得人称你是‘花中皇后’,一点不过誉!”想着、看着,竟轻声地朗诵起一首并不记得是什么人的七律月季花诗了:
只道花无十日红,
此花无日不春风。
一尘已剥胭脂笔,
四破犹色翡翠茸。
别有香超桃李外,
更同梅斗雪霜中。
折来喜作新年看,
忘却今晨是季冬。
“好诗,好诗!好声,好韵!”曹锟一边大声喊叫向她走来,一边轻轻地拍掌。
刘凤威神情一紧,转脸一看是老头子,有嗔有怒地说:“你做什么来了,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偷偷地听人家念诗来?”
曹锟笑着说:“自己的家,自己的夫人、太太,还要打什么招呼?念诗是雅兴,还怕别人偷听?”
“不正经!”说着,刘凤威便用手中的月季花瓣朝曹锟撒去。撒了他一脸一身。“你不在外边忙,跑来做什么?”
曹锟胡鲁着满在头面上的花瓣,一边说:“外边事办完了,忽然就想你了。特来看看你。”
“看我?!看我干什么?还是那个丑样。”
曹锟拉着刘凤威的手,一起走进小楼。
自从那日不愉快的听曲之后,曹锟便没有再到这座小楼来,刘凤威也赌气不理他、不下楼。她知道,曹锟宠爱她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三姨太陈寒蕊。所以,她自豪、自信,觉得老头子不会疏远她,他会到她身边来的。现在,他果然来了。她撒娇了,她不想理他,她走回楼里,故意背着身子,不去看他。
曹锟见她这模样,笑着说:“怎么啦,小东西?生我的气?”说着,把她拉到怀里,“我今儿没事,想听曲了,你唱个曲给我听听吧。”
“不唱。”刘凤威脸不转地说,“你没事了,我有事。”
“什么事?连曲也不唱了。”
“就是不爱唱曲的事。”
“别赌气了,快唱一曲。”
“我问你,这几天你到哪里去了?为啥连影儿也看不见。”
曹锟不想瞒她,于是,把去天津的事,把找王坦、王毓芝他们谈的“大事”简要地说一下,才说:“我都累死了,你还生气。你再不体贴我,我可更苦了。”
刘凤威一听是大事,破涕为笑了。“我错怪你了,曹大人。你大人不见小人怪,我给你赔礼了。”说着,给曹锟万了一“福”。
“唱个曲吧。”曹锟紧紧抱了她一下。
刘凤威也不挣脱,仰在他怀中,轻轻地唱道:
红杏深花。菖蒲浅芽。春畴渐暖年华。竹篱茅舍酒旗叉,雨过炊烟一缕斜……
“好了,好了。别唱了,别唱了。”曹锟摇着手说,“我有正事跟你商量。”“正事?跟我商量?”刘凤威惊讶了。“有什么正事跟我商量?”
曹锟简简单单地把花钱的事说了个来去,然后说:“不是想要你拿出钱来办多大事,只是大家人人都出一份了,你不出也不好。出多出少都不怕,出了就算对这事尽心了。就这个意思。”
提到钱,刘凤威犯了思索——实话说,这个十六岁进曹家的小女子,还真的对钱没有多经心呢。什么大钱、小钱,一到手就花光,没有了,自有人给,从不想积个什么累。嫁给曹锟之后,更是在钱堆里生活,有时竟想不出钱该怎么花。有一次,她领着女仆易了服装去游市场,兴致来了,竟在一个相士面相问卜。相士看了看她那副清秀素雅的模样,便有意奉承她几句,说:“瞧你这打扮,像个仆人;瞧你这贵相,必定是一位一品夫人!”
刘凤威十分高兴,随即拿出一百块大洋付给相士。
然而,在曹氏的各类实业中,刘凤威却不愿意插手。曹锟为她弄了私蓄,她才在天津北马路上的泉立成布庄投资十万元,别的,却一项也没有。听说曹锟又在什么地方为她购置了八百亩土地,地契给了她,地租归她收,她只委托人代管。在曹家的妻妾中,她算最穷的一个。所以,她听到钱事之后,眉头锁了锁,笑了。“曹大人,你不是拿小女子开玩笑吧?你自己最明白,连我身上有几两肉你也知道。这正是应了书本上那句话了,‘仓老鼠向乌鸦借粮——守的倒是难为飞着的’了。”
曹锟说:“我哪里是难为你,大不了要你表表心,有这番心意就完了。怎么会攀着你一定出多少钞钱呢?”
“那好,”刘凤威大方了,“到时候,你说个我能拿出来的数,我一定给。大人当大总统了,我受封也就心中无愧了。”
“谢谢小乖乖,我要的就是你这份心!”
曹锟还想再在小楼里呆一阵,正在此时,有人来报:“副参谋长王坦求见,说有急务!”他这才匆匆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