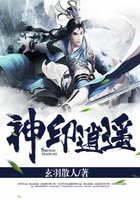夕阳下,轿车驶出了草原的花海草浪,以箭的速度射向梦中的沙漠。
我急于与夜晚的沙漠相见,谁知车在一个小镇上却停下了,换上了一辆八面漏风的破吉普车,司机也换了——由蒙古族歌手巴音换成了一个叫布和的老司机,他带上一副破手套,拉着我们摇摇晃晃上路了。
原来,轿车是无法开进沙漠的。只有吉普车和越野车是沙漠真正的征服者。
来之前,我问巴音要去的这片沙漠叫什么,他用生硬的汉语答非所问:沙漠,就是沙漠,我老家就在那里!
这位蒙古族朋友满腔热忱,但交流起来总是错位。我干脆啥都不问了,整理好皮箱由北京坐大巴去草原与他们汇合,然后一起向沙漠挺进。路上,巴音的女友诺敏告诉我,那片沙漠叫作浑善达克。
车上,还坐着一位面容消瘦的马头琴师莫日根,他一上车就抱着臂膀昏昏欲睡。他是巴音的朋友,也是搭档,他们来自同一座草原城市。我和巴音相识几年了,跟他却是第一次见面。如果我跟他很熟,一定会揪着他的耳朵将他揪醒,放着这么壮美的沙漠景色不看,真是暴殄天物。
四野渐渐空旷,植物稀疏,浑圆的落日将西天渲染得雄浑壮丽。吉普车拐入小道,长驱直入,连绵起伏的沙丘终于出现在面前,就像三毛作品中描述的那样:像成熟女性的胴体一样优美、性感,仿佛天外来物的景观扑面而来,让人瞠目结舌,如入幻境。
我生来热爱草原,此刻才知道,我骨子里更爱的其实是沙漠。沙漠一无所有却又应有尽有,我与它一见如故,那天长地久的默契不可言说。
夕阳在沙丘后沉落,夜的幕布徐徐拉开,天上的铜镜登场,它硕大明亮,漫天宝石般的星星摇摇欲坠,几乎坠弯了夜空——只有在沙漠中,你才能体会到星星是有重量的,不像我们在都市看见的那般飘渺虚幻。
月光下的沙漠像蒙面女郎,神秘、魅惑,即使置身其中,仍有种可望不可及的遥远。此刻,无论出现海市蜃楼还是天降异象,都不意外,此刻,让人相信奇迹。
破吉普车像袋鼠一样在沙丘上跳来跳去,这要命的历险使心一次次跳到喉咙,感觉只要一张嘴,它就能蹦出来。有心脏病的人,断然受不了这个刺激。突然,一只野兔从蓬蓬芨芨草丛中蹿出来,这带路的天使,很快就将越野车抛在后面,消失得无影无踪……
沙漠里没有明确的道路和方向,有两道车辙,基本就是一条路的标志了。要不是布和是一位当地的老司机,熟悉路况,我们肯定迷失在沙海中了。九月初的沙漠,晚上已经很冷,车内五个人挤在一起,还是冻得几乎咬不住牙齿。
车在沙丘间跳来跳去,颠簸得人渐渐有些恍惚,但小睡一会儿很快又会被颠醒。天色微明时,地上的草多了起来。到了一片铁丝网和木棍拦截的路口,巴音跳下来将木栅栏门打开,说:我家的牧场到了!
记得来之前我反复问过,到底是去草原还是去沙漠?在我心目中,沙漠和草原是两个概念,一棵草没有的地方是沙漠,水草丰茂的地方是草原。一望无际的黄沙中,哪来的牧场呢?没想到,沙漠中还真有牧场,有小片小片鲜花盛开的草原。
几间土屋孤零零地立在沙漠中,好像是大风随便吹来的。这儿是巴音七兄弟出生的地方,如今只有巴音的六哥一家三口住在这里,其他的或许在自己的牧场重新安了家,或者像巴音这样,彻底告别沙漠,来到草原城市求生存。
巴音的六哥六嫂已经烧好了奶茶、炖好了土豆牛肉在等我们。他们都是淳朴的牧人,皮肤黧黑,笑容灿烂,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屋内的陈设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只有生活必需品,没有一件奢侈品,除了那幅挂在正中的成吉思汗十字绣。桌子上摆着一个好看的花瓶,那已经是比较华丽的物件了,但里面插的是鸡毛掸子,而不是鲜花。也许,长年累月生活在这里,人已经没了那份心气儿;也许,他们觉得野花只有开在沙土中,才天经地义。
在屋内唯一的一套沙发上落座,吓了一跳,原来下面的弹簧坏了,坐下去弹不上来。幸亏大家基本都是瘦肉型的,否则,这沙发非被坐成一张皮不可。
旅途劳顿,菜还没吃一口,就要喝酒。用银碗盛着,旁边整齐地摆放着银筷子。我猜想这对蒙古人来说,应该是个很隆重的仪式了吧?只是大清早的空腹喝酒,是不是太野了点儿?我偷偷瞄了一眼,是六十度的草原白,不知胃是否能扛得住?黑黑的六嫂端着碗在一边等着,温温柔柔地劝让着:喝吧,喝吧,跑夜路冷,暖暖身子!
于是,把心一横,咕咚咕咚喝下去,灌小驴儿似的,噎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火辣辣的液体长驱直入,肚子立马火烧火燎起来,这酒就如同草原人,热烈得得让人受不了。用银筷子抖抖嗦嗦地去夹土豆,总是夹不住。扭头看看诺敏和莫日根,似乎也有点儿眼神恍惚,这都是酒的功劳。
六哥从车上拿来莫日根的马头琴,莫日根再三推让一番,也就拉了起来。看来他就这么个脾气,要他拉琴,必须大家再三请求才肯一显身手。他消瘦,长发飘飘,艺术家气质浓郁,是草原名人。巴音说他八岁时就参加马头琴大赛,获冠军,被视为神童。现在带了很多学生,桃李满天下。可是艺术上的天才,在现实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些低能,他迂腐、木讷、忧郁,除了拉琴,似乎对现实世界一窍不通。
别看莫日根总是显得很慵懒,半眯着眼,一副未睡醒的样子,可是一旦马头琴在手,就换了一个人似的神采奕奕,仿佛灵魂都附在了那几根弦上,每一根头发丝都放出光来。马头琴俨然成了他的情人,他们卿卿我我,旁若无人,每个人都因他的陶醉而陶醉,小声跟着哼唱了起来。
琴拉完了,莫日根也醉倒了。怀里抱着琴,蜷缩成一只大虾的样子,叫也叫不醒。六哥和巴音费了好大劲才将他弄到小木床上,盖上毯子,他已经鼾声如雷了。
酒桌旁的人继续喝下去。我感到自己的上下眼皮在打架,布和呢,困得直磕头。桌前只有我算是真正的客人了,我小心翼翼地提出撤席休息,谁知他们一听却又来了精神,说不行不行,必须让客人吃饱喝足。这些淳朴的蒙古人,外面世界对他们的冲击和影响很小,所以他们仍保留着待人接物的那一腔炽热,此刻,他们把它全倾注到我身上了。
我很后悔自己怎么不提前醉倒,还烧地瓜顶门——硬撑着,让人误以为我酒量很大。这下可好,他们要费多大劲儿才能将我醉至他们想要的程度啊?
醒来,已经是午后,沙漠的太阳热情地射到窗棂上。睁开眼睛,发现酒菜已收拾光,但人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吓得赶紧坐起来,暗骂自己怎么在这样的环境中就睡着了?来这儿之前就听说过,牧人家来客人时,常常是混居的,牧人天性率性豪放,没那么多房间,也没那么多讲究。但我这个汉人却无法适应,或许是齐鲁文化的渗透根深蒂固,或许是天性含蓄,与人相处无法如此的毫无顾忌。
赶紧爬起,喊醒其他人,然后郑重其事地收拾一番,准备与沙漠的初见。喝了六嫂煮的奶茶,迫不及待地去看门前的沙漠。不,应该说是牧场,沙漠中的牧场。
顺着门前的小路一直往前走,往前走,直到走到天地苍茫之中。巴音说:坏了,迷路了!
迷就迷吧!在自己的牧场迷路,那才是真正的传奇。
天蓝得耀眼,连一片云彩都感觉多余。脚下的草自然比草原稀疏,种类少而单调,都是些耐旱的植物:莲针草、芨芨草啥的,还有星星点点的小花璀璨着,连在这儿长大的巴音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草丛中有枯萎的树枝,痉挛般地伸向蓝天,不知是不是小胡杨?巴音说这儿的牧草比从前稀疏了,沙化越来越严重,牧场逐年被沙子吞噬着。如果环境继续恶化,总有一天这里会彻底变成沙漠,寸草不生。
爬到一个牧草扶摇的沙丘上,四周美得令人晕眩。太阳有点儿像南国的太阳,发出白炽的光,但并不歹毒炙烤,因为这广博的空间里充盈着干爽的清风,吹过来又吹过去,将炎热带走,留下说不出的惬意。风吹到身上爽爽的,不由想起闷热的江南,那种拖泥带水的潮湿,夏天黏黏的热和冬天直往骨头里渗的凉,才是真的惨无人道。
一阵马头琴声传来,举目四望,原来是莫日根坐在一丛芨芨草中,正忘情地拉着琴,似乎是即兴创作的曲子,幽怨缠绵,如泣如诉。他总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仿佛千钧的压力压在眉头。风吹起他的长发,使他那张如刀砍斧劈般消瘦的脸愈发显得苦情了。
听巴音说,同我们一样,莫日根也是父母双亡。我们是三个孤儿,大漠中的三个孤儿。就凭这,我们也要好好地相依相扶着将以后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好。巴音与莫日根是搭档,他虽以唱歌为生,口才却实在不敢恭维。很多话吞吞吐吐讲半天,也让人听不出个所以然来,倒是他新婚的媳妇诺敏心直口快,间或替他当当发言人。这几个蒙古朋友颠覆了我对蒙古人的印象。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多少粗犷、豪迈、奔放的影子,他们大都木讷寡言,和现实世界也有些隔膜。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那是一个即使是朋友也无法进入的世界,令人不时有对牛弹琴的错位感。不知是文化差异还是性格差异?
这片人迹罕至的沙丘,连一粒鸟粪都没有,显然连牛羊也未曾涉足过,干净得如天地刚诞生时的样子。在这艳阳高照的正午,一切都在沉睡,静谧得让人孤独。
沙丘下的植被似乎比上面更茂盛,有些蓝色的野花在其中摇曳闪烁。巴音说,他不知自己家牧场的尽头在哪里,因为他从没到达过。牧区在计生政策最严苛时也是自由的,孩子能生多少是多少,一个人能分得几百亩甚至几千亩牧场,人口多的,牧场就大得望不到头。这些年,牧民的生活日渐富足,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吉普车、拖拉机,成群的牛羊就更不用说了。
用手拽着芨芨草往沙丘下走,一步步小心翼翼,鞋里很快塞满了柔软的沙子。大家干脆双手抱头,叽里咕噜地滚了下去。躺在热烘烘的沙地上回望着方才那个沙丘,线条优美得就像鸡蛋一样,又如一只饱满的乳房,那是风长年累月精心雕刻的造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词穷。
看累了,这几个迷路的人才开始一筹莫展,该如何寻找回家的路呢?
早晨,蹲在六嫂家门前的沙地刷牙,成群的鸟儿在不远处嘀嘀咕咕,起起落落。它们每天早晨必来,不早不晚,就在我刷牙的时候。是不是看一个陌生的都市女子出现,它们也好奇呢?
我边刷牙边四处张望,不远处,摞着一圈儿牛粪。足足有半个草垛那么大,那是冬天取暖用的。牛粪其实是牛消化过的草,按说并不脏,但再干净也是牛粪,不是鲜花。没有鲜花的香味儿,更不可能有鲜花的艳丽。
六嫂家靠房后日夜旋转的风车发电照明,吃的水是从很深的井里打上来的,冰凉。上面的世界与下面的世界冰火两重天。再热的沙漠,在地层深处也有幽凉。
当游牧民族相遇农耕文化,会有怎样的对比与落差?应该说,牧民生活要比农民悠闲潇洒得多,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生土里刨食,为土地所累。牧民呢,赶着牛羊在草原上游荡,走到哪儿哪儿是家,不用种,不用收。现在放牧方式改变了,不再游牧,每家都有了固定的牧场,四周用铁丝网围起来,房子就盖在自家牧场里,牛羊也只在自家牧场范围内啃草游逛,不再进入其它领地。牧民只需每天早上将牛羊赶出圏,赶到草多的地方,就可以回家,爱看电视看电视,爱打扑克打扑克,爱睡觉睡觉。夕阳西下时,再去把羊群领回来,或者它们自己在头羊带领下,慢吞吞地回家。秋草黄时收割好,羊儿又有吃的了。就这么简单。
常住在沙漠里,单调乏味。在这里,寂寞亘古不变。一件事,不知酝酿多少天多少年才有质变。一个愿望的实现,有时需要等上一生,才能有个回音,甚至一生也无消息。时间是缓慢的,有时甚至让人觉得这儿已经被时光遗忘。在静默之中,谁也不知道什么会发生,什么将永无变化。在这里不用上班,不用打卡,一旦放松了,恨不得将欠下的觉都补上,但一醒来,却是渺渺茫茫的空虚与怅惘。
这天,六嫂说,我们一起去敖包吧,许个愿,一切也许就会好起来。顺着门前的小路一直往前走,就会出现一个小山坡,敖包就在那上面。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哟喂,
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哟……
在这首著名的《敖包相会》中,敖包是热恋中的男女约会的场所。
一直以为敖包是另一种蒙古包,其实它不过是用石头垒砌的一个小包。上面插着树枝,树枝上飘着五颜六色的哈达,已经被风雨漂得陈旧。蒙族的敖包与藏族的玛尼堆相似,不过玛尼堆是佛教的产物,石头上多刻有经文,与藏族转山祈福的习俗有关。敖包则是萨满教的产物,位置多是固定的,有祈福兼路标的作用。这是我见到的最高的敖包,不知道多少年垒积的石头才形成了它的高度。
在山包上举目四望,四野苍茫。美丽的野花,干枯的植物,还有个小得像眼睛的湖,湖边有很多白色鸟儿。六嫂说,那是天鹅。
围着敖包顺时针走几圈儿,再逆时针走几圈儿,这都是有讲究的,蒙古人心目中的长生天,是汉人不能理解的另外一番境界。
转完了,将事先捡来的石头放到敖包上。大家一起跪在敖包前,许愿。谁也不知谁许下的是什么,但每个人都郑重其事。大家都站起来了,莫日根还跪在那里,闭着忧郁的眼睛喃喃说着什么,额前鬈曲的头发在漠风中飘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