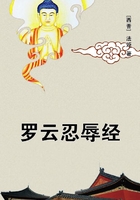战况吃紧,圣旨下达以后,袁靖阳不顾有伤在身,立刻召集大军挥师北上。
三十万大军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车辚辚,马萧萧,旌旗蔽日,烟尘漫天。前锋队伍分成五个列队,中间有一面猩红色的大旗,上面写着“镇国大将军袁”,正迎风猎猎招展。
队伍如洪流般滚滚向前,一群群低伏在草丛中的兔子受了惊吓,撒着腿儿胡乱奔散。
秋日的平原,生长着齐腰深的蒿草,抽出白花花的穗,在落日前的微风中摇曳。然而经过无数车马的撵辄,战靴的踩踏,变成了灰白色的碎末散落在浮土里。
最前面是百来人的小股侦察部队,始终和大部队保持三十余里的距离,每一刻钟就有一匹马飞驰过来,向主帅袁靖阳通报前方的情况。
前三天,队伍行进还算顺利。到了第四天,天气就变了。
云层低垂,阴冷的北风嗖嗖刮了大半天,午后下起雨来。豆大的雨点,落在干燥的浮土上,先是砸出一个个小小的坑圈,溅起尘埃。没多久大雨便洋洋洒洒,从天而降,整个平原形成了一帘浓墨重彩的秋日雨水画。
满载军粮的车轮陷在水坑里,士兵们涨红了脸,齐声喊着号子向前推,不时有人“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爬起来满身是泥。
战马口吐白沫,马夫用鞭子拼命抽打,眼看就要把车轮拖出泥辄了,突然脚下打滑差点失蹄,车轮又在高处重新退了回去,更深的陷入泥潭中。
袁靖阳心急如焚,离靳州尚有五百余里。靳州告急的文书一张接着一张地收到,求援的心情一句比一句急迫。
“……靳州成孤城已月余矣,每日攻城之贼兵数不胜数,黑压压蚁匐于城墙,箭雨如蝗。初贼兵三日一攻城,近日渐成每日一攻,甚或夜间亦有明火执仗来犯者。在下拼死抵抗,虽重创辽夷于靳州城下,然靳州之围愈急矣。眼见守城之军士逐日减少,伤者彻夜呼号,惨不忍闻。城中粮食已尽,谣言四起,百姓惶惶。在下日日登城南望,盼大将军神兵忽至,解靳州水火之急。何曾见大将军一兵一卒呼?今靳州危如累卵,城破之日,唯有举刀自裁,以报皇上知遇之恩……”
袁靖阳脸色阴沉,剑眉紧锁,竟然把下唇咬出一道深深的牙痕。
靳州,是一个战略枢纽,扼守着身后广袤的平原。其战略意义,双方主帅再清楚不过。
它是大辽通往中原的北隘口,一旦靳州失守,几百里富饶平阔的土地再无险可依。一旦把这里作为主战场,辽军几乎全是马队。正好可以发挥辽兵机动性强,用重型骑兵集团冲击宋军的战略意图。
辽兵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限,宋军的步兵不可能抵挡得住这样强悍的冲击,一旦溃败,战局失控,几十万人成为任人宰割的牛羊也未可知。
靳州不容再失。
袁靖阳决定亲率五万精锐,暂离大部队,急行军星夜驰援靳州。
征讨副将秦俊,在袁靖阳离开后,将接替主帅指挥大部队。两人约定,袁靖阳先行,大部队随即跟上,用飞鸽传书,半个时辰互通一次军情。
出师不利,前途未卜。
袁靖阳苦笑,在自己的国土破击贼寇,竟然需要劳师远征。五万疲惫之师就是赶到了靳州,战斗力也不足一半了。天时,地利,人和,竟然一条也不占。要是后继部队跟不上,五万人无疑是羊入狼群。
这仗,打得过于凶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