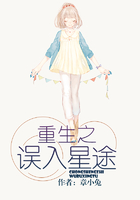当然,知识分子中不乏关注现实、感时忧国、心系苍生的人,而许多知识分子本来就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他们成为知识分子之前,本来就属于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譬如老三届一代出身的知识分子。但问题在于,当他们进入“话语圈”,以“话语”的方式来表达时——如前所述,非如此,他们就不能获得知识分子的印记,不能获得学术文化体制的承认。——话语所寄生的思想、主义、体系、知识、概念,已经形成了一个无法逃脱的话语规则和表达策略,限制、改造甚至阉割了他们关注现实的精神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体验。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学术圈中不断掌握各种“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当代真实生活时,会感到那样困惑和匪夷所思。我们所拥有的话语既不能解释、说明社会的真实、真相,更不能改变社会的面貌。所谓“民间立场”“平民意识”,说到底也不过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话语。因为在话语系统里,民间、平民“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语)。而“话语圈”中知识分子的表述,与真实生活中的他们相距甚远!可叹的是,我们中许多人还自以为是启蒙的“精英”,是人民大众代言人,自以为自己的话语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呼声、要求、愿望呢!因此,我想给包括自己在内的“话语圈”中人提个醒:“话语”固然有其学术化价值,但在现实面前,在说明世界和改造世界面前实际上是十分苍白无力的,种种“精英”“启蒙”之类的自恋、自大都是非常可笑的。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关注民瘼苍生的知识分子,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也要发出来自生活和民间本身的声音,则需要走出“话语圈”的胆识。左拉说过:“为了确信我在生活,我需要铁锤打在铁砧上的音乐。”我也想说:为了确信我在生活,我不需要“话语”。
拒绝遗忘“文革”
——我的一次课堂经历
这是一次平常的文学理论课,我给中文系学生们讲授的内容是“诗歌体裁的美学特征”。当我说到诗歌文体的精炼、简洁特征时,忽然想到安徽著名诗人韩翰的小诗《重量》:
她将带血的头颅放到了天平上,
使一切苟活者失去重量。
这首诗作者写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当时众多的以张志新为题材的诗篇中,这是最短的一首,但却以最凝练的形式和丰厚的内涵的统一获得了全国诗歌奖,并广为传诵,因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以该诗作诗歌文体精炼、简洁的例证,是非常恰当的。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首诗的内涵,我打算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张志新其人其事。在介绍前,我有意识地问了一句:“你们知道张志新是什么人吗?”全班同学竟无一人作答。我还不死心,又抽问了几位同学,大家皆摇头,一脸茫然。有的同学甚至在座位上发出窃笑,似乎是觉得我老是追问这个问题有点可笑。
我的心不禁一阵悲凉。站在讲台上,我想得很多,思绪再也无法集中到“诗歌体裁的美学特征”上。我想,就算是“跑题”,我也要给学生们说说张志新。于是,我说到张志新是一位在新中国成长的美丽、聪慧、善良、情感丰富,富有生活情趣的知识女性,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文革”时代,作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勇敢地公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不仅使天下男人汗颜,也使一切“做稳了奴隶”的中国的“苟活者”汗颜。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为独立思考、捍卫真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她被绑赴刑场时,刽子手们害怕她仍然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残忍地割断了她的喉管……
教室里一片寂静。学生们全都睁大了眼睛,静静地在聆听着我的介绍。有的女生,眼眶里含着泪珠。
“难道我们不知道和遗忘这样的人不是一种悲哀,甚至是一种耻辱吗?”我以这样的反问结束了自己的介绍。话虽说得有些重,我发现同学们的表情却十分肃然。
我又有些感动了。当代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们,并不如一些媒体和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都属于“嬉皮士”“雅皮士”“美眉”“另类”,他(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在言行上有时表现出玩世不恭、游戏人生,但在内心深处仍然是追求理想、向往崇高、崇敬英雄的。所以,当他(她)们了解了张志新的事迹,便顿时产生出一种对为捍卫真理而献身的英雄的敬畏之情,如同他(她)们对屈原、文天祥、谭嗣同、鲁迅、闻一多等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的崇敬。然而,在此之前,他(她)们确实不知道张志新,甚至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这难道仅仅是他(她)们的过错吗?
我们的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与商业文化的合谋。传媒、电视和图书里的历史,或是以清宫戏为代表的帝王将相的历史,或是“红色经典”再现的历史,甚至“样板戏”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被再次搬上舞台、银幕,唯独“文革”这场人类历史上的大浩劫,难觅踪迹。因为这既符合意识形态淡化、消解“文革”历史的意愿,又投合商业文化娱乐消遣休闲的消费需要。无论是前者的“一切向前看”,还是后者的“一切向钱看”,都需要对“文革”的遗忘。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或大学生,你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像熟悉慈禧太后、康熙大帝那样熟悉“文革”和张志新呢?因此,当问张志新是什么人,他们除了一脸茫然,又能怎样呢?
如此一来,不要太久,当亲历“文革”的人们故去之后,“文革”岂不真的要被一代人彻底遗忘?这意味着什么呢?冯骥才在《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附录里记录了几位“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请听听其中的几段:
一位大学一年级男生说:“如果叫我回到文革,我不反对,甚至很有兴趣。一是我不觉得文革怎么可怕,二是可能会感觉很新鲜。”
另一位高二女生说:“我想多了解文革,不知从哪里去了解。”
一位年轻的出租车司机说:“文革咱没见过,但比现在强!”
一位大一女生说:“那个时代有激情……现在无法生活得那样富于激情了。”
我想,如果他(她)们了解了张志新、遇罗克等人的故事,还会这样认为吗?
无论是作为“文革”亲历者,还是人文知识分子、学生们的老师,我都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要把“文革”的真相,“文革”的危害和影响告诉同学们,我都要对同学们说:不要忘记“文革”。拒绝遗忘“文革”,就是拒绝“文革”悲剧重演。
于是,我在课堂上仿佛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时代,向同学们简要地讲述了“文革”的来龙去脉,介绍了新时期文学中反映和表现“文革”的文学作品,介绍了巴金的“要建造一座文革博物馆”的庄严呼吁,介绍了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片断……
教室外有人在唱着甜腻腻的流行歌曲,对面商业大楼上披挂的各种广告条幅赫然在目。说着说着,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孤独感。仿佛有人在耳边对我说:你说这些,难道不觉得不合时宜吗?
下课了,一位女学生走到我面前,说:“老师,我想从您那儿借《一百个人的十年》看看,图书馆里借不到这本书。”我欣然答允。我刚走出教室,听到一位男同学正在大声朗读我刚才介绍的北岛的诗《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质疑“实话实说”
很小的时候,大人们就对孩子说: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不撒谎、讲真话、诚实。这几乎是所有儿童接受的启蒙教育。所以,才有了“童言无忌”,才有了《皇帝的新衣》里唯一从孩子口中发出的“皇帝没穿衣服”的声音。遗憾的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是一个由成人支配的社会,成人们为各种各样的利益、需要、欲望、目的所驱使,不断地制造着各种各样的谎言,欺人与自欺。更遗憾的是,儿童总要长大成人,而一旦融入成人社会,你和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讲假话。而当整个社会都在讲假话,譬如“文革”时期,除了《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作为成人,谁又敢站出来揭示事物的真相呢?凤毛麟角者有,如遇罗克、张志新、顾准等,但其命运,是大家早已知晓了的。
就这样,由成人支配的社会说假话,说假话的社会又造就了更多不讲真话的成人,如此循环不已。故鲁迅痛切地说中国是一个“瞒和骗的国度”。说假话的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文革”中走过来的“思考的一代”才发出了“我不相信!”的宣言。因此,打造“诚信社会”,成为今日重建信仰、信念、信任的第一要务,而具体的落实就是:从上到下,从官到民,从大事到小事,都要讲真话。
正是出于上述这一切,一些年前,当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推出谈话类节目《实话实说》时,确实激动不已。我觉得它的出现本身是一种标志,标志着对曾经的“瞒和骗”的历史反思,对诚信社会、对讲真话的呼唤和倡导。虽说它只是电视的一个谈话类节目,但由于其所处的主流媒体位置,“实话实说”的旗帜对于社会风气的改善和人们行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所以,这些年来,我始终是《实话实说》的最忠实观众,几乎一期不漏地收看。应该说,该栏目由于编导的精心策划,几位优秀主持人的主持,使它深受广大电视观众欢迎,已经成为央视收视率较高的一个品牌栏目。特别是在栏目创办初期,确实体现了“实话实说”的风貌,使国人为之一振,奔走相告。首先,那些期的选题都是“实话”,即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普通百姓关注、忧虑、困惑的,而又常常为有关方面回避、淡化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话题,如贪污腐败、社会治安、下岗工人、官僚主义、爱情与道德等。其次,针对这些“实话”,栏目确实做到了“实说”。这既体现在主持人的倾向、嘉宾的态度、现场观众的反应上,更体现在他(她)们谈话的方式和内容上:开门见山、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不回避问题、矛盾,谈事论人,一针见血,且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问题的要害,不怕犯忌。许多观众在观看中常常忍不住击节而起,他们觉得“过瘾”,因为栏目说出了他们或是没有想到或是想到不敢说的真话,而这些真话又是上关国计民生、下关社会风气的“盛世危言”,决非阿猫阿狗、一地鸡毛的闲话。
然而,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是何缘由,《实话实说》栏目渐渐变味了。初期的锋芒没有了,初期的严肃性日益被搞笑娱乐所代替,初期的人文关怀精神日益被游戏态度所消解,初期的对社会问题、矛盾的正视,对社会难点、热点、焦点的关注,越来越让位于四平八稳的、无关痛痒的、鸡毛蒜皮的、开心一乐的话题和言说。尽管主持人仍然是优秀的,尽管我每期仍在收看(毕竟这个节目的独特性是其他节目所法替代的),但在我的印象中,《实话实说》背离它的初衷似乎越来越远,已经越来越像是一个综艺娱乐类节目了。
这当然也无妨,或许收视率会更高。但既然栏目冠之以“实话实说”,而出于主流媒体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和人们对讲真话的期盼,面对今日的《实话实说》栏目,我们就有理由质疑:首先,选择什么样的“实话”来作为言说、谈论的对象?是热衷于那些无关痛痒、无伤大雅、琐碎平庸的,甚至粉饰现实的所谓“实话”,还是关注和选择那些百姓普遍关心的而又常常由于各种原因被掩饰、淡化的社会真相、问题、矛盾、热点、难点、焦点,作为真正的“实话”话题?其次,“实话”如何才能做到“实说”?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轻描淡写、言不由衷地说一通,甚至以游戏方式来冲淡真实的严峻,以搞笑态度来稀释真话的锋芒,还是正视实话,说透实话,说得有些人坐不住,说得有些真相再也无法掩盖,说得有些假话再也无法欺人与自欺?总之,在我看来,优秀的、名符其实的“实话实说”节目,一是说的确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实话”,二是“实话”确实“实说”。二者缺一不可。而现在的该栏目,在这两方面都有待反思、改进。观众对《实话实说》栏目的这种批评和要求,本身就是一种“实话实说”,它一方面体现了广大电视观众对央视品牌栏目的热爱和呵护,更重要的,如前所述,人们对于这个栏目的特别关注,表达了大家对于“人人愿说、能说真话,真话真说”的一种期盼和呼唤。说到底,“没有有效的反对意见,民主制度便无法实现”(李普曼《不可缺少的反对派》)。
附记:当我这篇文章写后不久,央视《实话实说》,还有《读书时间》等栏目已被取消,栏目的几位主持人也开始主持收视率更高的娱乐类节目。这真是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啊!